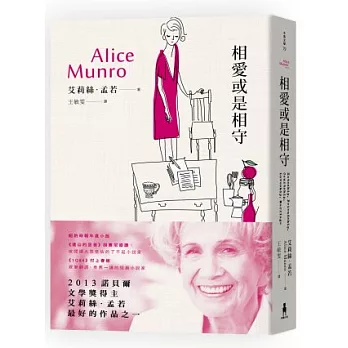對於我,書袋是閱讀障礙,一是覺得為什麼不大方用自己的話說就好,拉個名人來幫忙發言會比較有說服力嗎?二來是,我跟這名人或名句不熟,因此非但沒有增加說服力反而增加陌生感,徒增困擾。
及至最近聽廣播,顏擇雅小姐解釋她「掉書袋」的用意,原來這是一種「另類閱讀」的方法。
她心目中理想的掉書袋有幾種方式:
一.有話要跟對方講
不是用別人的話來幫我說話,而是我有話要跟對方說。比如911讓她想到愚公的個人偏執:「雖我之死,有子存焉;子又生孫,孫又生子;子又有子,子又有孫。子子孫孫,無窮匱也。而山不加增,何苦而不平?」《列子•湯問篇》顏擇雅覺得愚公很可怕,他只看到自己的「有志者事竟成」,他看不到「人各有志」。
二.作者沒有明講,以致大家引用時都誤解了作者的意思,她想為作者澄清。
目前10英鎊鈔票上女王背後是珍.奧斯汀的頭像,且引用了她在《傲慢與偏見》的一句人物對話:「閱讀真是無上的娛樂啊!(I declare after all there is no enjoyment like reading!」,看起來沒什麼問題,但如果妳是書迷便會知道這是出自喜歡男主角達西先生(Mr Darcy),但愛慕虛榮不喜文學的卡洛琳.賓利小姐(Caroline Bingley)之口,其實是在嘲弄文人腐儒的反話,而非真的喜歡閱讀。三.發現古人的矛盾
例如她的一篇文章《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》,康德覺得請客吃飯是「最高道德兼自然之善」,但孔子卻認為「樂驕樂,樂佚遊,樂宴樂,損矣。」顏擇雅的看法和康德一樣,她舉康德為例想告訴孔子:只要動機恰當,方法正確,「樂宴遊」也可潤身又潤心。整個聽下來,讓我對古人和老生常談的故事,有了新的體悟。
我的書袋
回想自己,會掉書袋嗎?掉什麼樣的書袋呢?有些時候,如獨自洗碗的瞬間,思索剛才吃飯時大家的閒聊,談到某某人事如何,當下覺得癢癢的,然也不知道說些什麼,點個頭微笑讓談話有個結束。及至洗碗時,才想到,啊!其實那個誰或那個故事裡,不也曾如此...
其中的細節、感傷、在意,對這「人」說,不用話說從頭,不用舖陳。
我的書袋,是寂寞書袋。